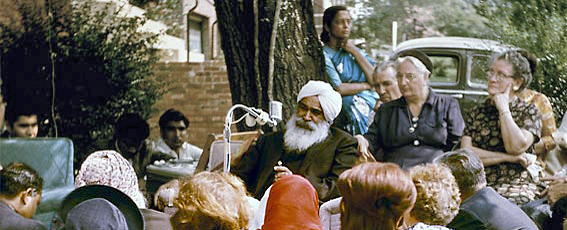上帝之道
回歸上帝的道路非人類所造,而是上帝,而此道路毫無人為機巧、矯揉造作的成分攙雜,上帝藉著祂揀選的人–神人–將人拉回祂自己的身邊,直接向神人揭示這條道路(上帝之道)的秘密,或經由聖薩特古魯為利益人們而顯現此秘密。
全世界各地的明師、彌賽亞、老師和先知以兩種類型降臨,其受指派的使命各有不同。有一類,他們唯一的目的只維持這世界的和諧運作;另一類,他們受命將已經成熟可回故鄉,且又渴望早日回到「靈性源頭」的靈魂引領回去,在他們往下漂泊來此物質世界之前,他們已離開此「靈性源頭」許久。在第一類中,所有的改革者降臨;第二類中,如聖人(Sants)與薩德(Sadhs),他們具有揭示上帝知識,並將上帝力量示現在人身中的權能。
往上回到源頭與向下到此物質世界的過程相反,因此,在啟程前往「大生命之海」,回歸故鄉的內在旅程之前,人必須重建自我,將其所有徘徊遊蕩的智力聚集到靈魂的不動點(the still point),即位於兩眼之間後面的時間與超時間的交叉點內。事實上,這一向都是各處所有聖賢和先知唯一的主旨,然而,他們沒有一個人會想建立任何新的宗派或制度化的宗教。在談到世上存在如此多全然令人困惑的理論與互相抵觸的教義時,哈祖爾巴巴薩望辛吉瑪哈拉吉(hazur baba sawan singh ji maharaj)常說:「已經到處存在這麼多井了,人何必再挖掘更多的陷阱,讓困惑更形混淆呢?」
上帝以祂自己的形像造人,人則以自己的形象創造宗教,並以其熱情造出各種崇拜物。真正的宗教在其成立以來,簡樸清新而未經加工過,就像初生的嬰兒,充滿著生命活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如其它所有事物,發展成一種制度或習俗,因此開始腐敗,而逐漸失去其原本的生命靈活度,此生命靈活度即源自於明師靈魂充滿生氣之聯繫;而漸漸形成一種社會經濟的外貌;宗教不再像人與人之間輕柔聯結的愛一樣來服務人,反而成為持續撕裂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衝突、仇視和憎惡的根源。當人類的苦杯滿溢的時候,為了被衝突爭鬥撕裂的人類,救世主就會帶著希望、救贖與滿足願望的訊息降臨;為重建人類價值觀上的平衡,他設法撫平惡化的社會傷口,向人類宣揚一體與平等;同時,他的主要目標是拯救人類的靈魂,使其有更高等的目的,就是過一個不同於肉體生活的真正的靈性生活,這的確是佐羅斯特(Zoroaster)、瑪哈威拉(Mahavira)、佛陀(Buddha)、基督(Christ)、莫罕默德(Mohammed)、卡比爾(Kabir)與拿納克(Nanak)等偉大的明師的目標,他們各自在自己的時代,遵照當時普遍的條件和人們的渴望,因為他們總是設法用阻礙最少的方式引導他們,一點一點的發放給他們可能正需要,也適宜作精神補給的基本養分,以便在靈性進化或拓展的過程中邁向更高處。聖人為一般人類所做的事是,讓他們從內邊靈性的大儲存槽中獲得鼓舞,對所有人皆是如此。
豐富的遺產
現代印度的宗教思想中,十四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中葉這段期間,是其中一段有顯著影響的時期,這段期間,著重在使宗教重新定位,並展現其最簡單的形式,即真正信仰、博愛與真誠奉獻的形式,以抗衡導向偏執與盲從的教士般的儀式主義與狂熱之苛嚴行為。
這期間我們找到像拉瑪蘭達(Ramaranda)等偉大的老師,他有來自各階層的弟子,(拉加皮帕Raja Pipa、補鞋匠拉維達斯Ravidas、理髮師賽納Saina、織布工卡比爾Kabir、賈特人達納Dhanna 、Narari、蘇卡帕馬瓦蒂SukhaPadmavavati、蘇蘇拉Sursura及其妻子等);瓦拉巴恰亞(Vallabhacharya),克里希納(Krishna)崇拜者的著名代表;孟加拉省納地亞區的柴坦亞瑪哈普拉布(ChaitanyaMahaprabhu),他以著重哈利波爾(Hari-bole)或頌唱上主的名為特色;瑪哈拉希特拉省的印花棉布工納姆德夫(Namdev);以及北部偉大的卡比爾(Kabir)與拿納克(Nanak);他們都不非常強調偶像崇拜和外在宗教形式與象徵的奉行,其永恆不變的論題為自我的純淨、愛與內在的呼求。
納姆德夫說:
要愛那位充滿我心的人,千萬不要與他分離;
納瑪(Nama)已將他的心與「真名」聯繫起來。
如同孩子與母親之間的愛,
我的靈魂也是這樣沉浸在上帝之中。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都一樣成就了那項「目的」,
在那目的裡面沒有絲毫分別的標誌。
他又說:
人進入天堂
不是靠禁食、重複祈禱文與信條,
如果了悟真理的話,
麥加寺廟的內在遮蔽物就在人的心中。
拿納克也說:
在這不純潔的世界上保持純潔,
你才能找到通往宗教的路。
然而,這場運動在卡比爾(1398-1518)和拿納克(1469-1539)的照料下達到了它的巔峰,他們倆幾乎生活在同一時代,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是同時代的人。他們擺脫世俗的束縛,跨越宗教的藩籬,因此受到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兩者共同的讚揚。他們的教誨主要聚焦在上帝與人,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上,兩人都是「蘇拉夏白德瑜珈」(SuratSbabd Yuga)(音流瑜珈或聯結神聖的「沃德」的瑜珈)的弘揚者,他們的著作也讚揚「蘇拉夏白德瑜珈」為生命之冠。如果我們在任何宗教自身原始的純度與真實之中,如同明師原本的話語中所呈現的那樣(他們自己實際練習,以及他們傳給他們所揀選的徒弟 - 古魯沐克或使徒–的東西),來研究那些宗教的精髓,我們一定會深刻的見識到,無論他們是在什麼層次上,他們全都是某種形式上超自然之「看」與「聽」的提倡者;然而,對於一般人他們仍然只用比喻的方式傳遞他們精微的思想,因為不這樣,一般人就聽不到他們的教誨,更難以理解他們的教誨了。
這種世界老師就像生命海洋風暴中的燈塔一樣提供服務,試圖將掙扎於時間流沙中的人類拯救出來。他們因為是光的孩子,所以他們為驅散靈魂的黑暗而降臨,自然被稱為「古魯」,即黑暗的驅除者–黑暗源自無知於生命真正的價值。他們對所有的宗教與宗教領袖都持有無邊的愛,對所有的經典都同等尊重。他們的擁抱是全體性的,一次長掃即把整個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類納入懷中,將他們平等的浸入上帝之愛中。.
卡比爾這樣告訴我們:
所有我們的聖賢都值得推崇,
但我只向精通「沃德」的人誠心奉獻。
祂更進一步告訴我們,為了人類的利益,祂帶著神聖的訊息,從一個時代轉世到一個時代,祂在全部四個世代(Yugas)或時間的循環中出現:首先以薩蘇克拉特(SatSukrat)的身分,然後以卡魯納邁(Karunamae)的身分,再以穆寧德(Maninder)的身分,最後,在現在時相中以卡比爾的身分出現。
拿納克古魯也不斷告訴我們蘇拉夏白德瑜珈作為救世之道的重要性與無上的功效:
像蓮花從泥池中挺立而出,
或像高貴的天鵝,高飛出水而乾爽不濕。
同理,人一旦與沃德聯結,就能毫髮未傷的穿越令人畏懼的生命之洋。
簡略的說,這是創世紀以來給我們的一個重大訊息,吟詠出通往上帝的道路。所有的印度聖人與基督的神祕主義者都練習過這門內在的「科學」,透過此內在的生命線與各自的靈魂接觸。當人們忘掉這項事實時,上帝的恩典就在一個被稱為聖人的體內自我顯現,在漫長的永恆路上,引導誤入歧途的人類。這是「至高無上者」授予的優越特權,這項權力也根據祂的訓喻傳遞下去;「風吹到它想吹的地方」;沒有人能夠制定或預言這種傳承的規則、地點或時間。.這項豐富的遺產從眼睛到眼睛傳遞下去,既不受傳統「加迪斯」(所謂成聖的座位與聖地)的限制,也不依賴人類世俗事物或教士聲譽的認可。活動於卡塔坡的拿納克古魯,將靈性遺產傳給白雷納,他以安加古魯(GuruAngad)的身分移居到卡督薩希;而他的繼承人阿瑪達斯古魯(GuruAmarDas)則被迫遷居高茵得瓦爾(Goindwal);由於拉姆達斯古魯(GuruRamdas),於是產生了「阿姆里察」,而後成為阿將古魯(GuruArjian)的總部。因此可見,像那類的地方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聖人在某個地方度過他們的一生,人們應該將它們的神聖,歸功於聖人神聖的影響;「奉獻誠心的地方,都是神聖的地方」;不是地方使人獲得榮耀,而是人使地方獲得榮耀。
重新尋回丟失的線
生命之流在永無止境的時間之中,無休無止的滾滾前行,此「無限」的力量在相對的世界裡出現後又消失。
在描述巴巴賈瑪辛吉(BabaJaimalsinghJi)的生平之前,值得我們大致回顧一下造就他的背景。確實,無論他做什麼,在什麼地方做,都是索米吉(SoamiJi)的力量透過他在運作,因為他已完全失去自我,臣服於他內邊的上帝之中。
為便於從適當的角度瞭解事情,並與我們靈性遺產的歷史聯繫起來,我們必須回溯至高賓辛古魯(Gobind Singh,1666-1708)的時代,他是拿納克古魯一脈相傳中十位古魯的最後一位。
一位拉坦饒貝須瓦(Ratan Rao Peshwar)的王后,由白難拉爾(Bhai Nand Lal)陪同來到高賓辛古魯的足下尋求庇護。(2)
高賓辛古魯遊歷很廣,曾深入北部的喜瑪拉雅山和南部的德干高原(Deccan)。廣泛遊歷期間,他和所遇到貝須瓦的掌管家族生活在一起,並印心了其中一些家庭成員進入此內在的科學。據說貝須瓦家族的一位拉特納嘎饒(Ratnagar RaO)接受了印心,並被授權繼承高賓辛古魯的工作。夏姆饒貝須瓦(Sham Rao Peshwar),是巴吉饒貝須瓦(Baji RaoPeshwar)的長兄,後來的掌管者;他一定曾與拉特納嘎饒有所聯繫,他在靈性的道上顯現了非凡的資質,而取得迅速的進展。過了一段時間,這位年輕的皇家後裔在距離烏塔普拉德需邦(Uttar Pradesh)的阿格拉(Agra)三十三英里的哈斯拉斯(Hathras)安頓下來,他就是後來的吐爾斯薩希(TulsiSahib,1763-1843),葛特拉瑪雅納(Ghat Ramayana)(彌滿於人與自然中的內在生命本源的科學)一書著名的作者。靈性生命的燈火(VitaLampada)繼續由吐爾斯賽希傳給了索米席夫達雅辛吉(SoamiShiv Dayal Singh Ji,1818-1878)。
哈斯拉斯的吐爾斯賽希與阿格拉的索米吉之間的聯繫似乎被忽視了,但這幾乎是沒有疑問的。從巴巴蘇蘭辛(Baba Surain·Singh)的手稿敘述,查查帕塔辛(Chacha Partap Singh)所著的「吉梵查里塔吉索米吉瑪哈拉吉」(Jivan Charitar Swamiji Maharaj),以及由希里SD馬赫希瓦里(Shri S·D·Maheshwari)所著的「與一些美國人的通信」中,可以瞭解到索米吉的父母是哈斯拉斯聖人的徒弟,而且經常去他家親近他,只要這位哈斯拉斯的聖人去到阿格拉,就去聽他講道;拉拉迪瓦利辛賽斯(LalaDilwali Singh Seth)的兒子都是他命名的,即席夫達雅辛(Shiv Dayal Singh)、布林達班辛(Brindaban Singh)和帕塔辛(PartapSing)。長子出世前,他預言有位偉大的聖人將要示現在他們家,而且這位長子出世後,他告訴父母親,他們再也不必來哈斯拉斯了,因為萬能的主已來到了他們當中(3)。
這位哈斯拉斯的聖人帶著熱烈深切的關注,按照自己的模子鑄造索米吉的生命,他在這年幼的小孩很小的時候,就為他印心;索米吉在生命最後的一天,告訴他的徒弟,他從六歲開始就已練習這門內在的科學。(4)
從索米吉的生活中,可充分看出他對哈斯拉斯聖人的敬仰·他對吐爾斯薩希的弟子們非常尊敬,其中尤其敬重吉爾哈里達斯薩度(Sadhu GirdharicDass),他在吉爾哈里達斯的晚年扶持他;有一次,這位薩度病倒在盧克諾,與內在的音流失聯了(想必是因為過去的業障)。索米吉趕快從阿格拉趕去那兒,在他死前幫他接通內在的音流(「索米·吉傳」,33-34頁)。
另外,索米·吉經常從他偉大的前輩的生活中舉例給他的追隨者,教導他們忍耐性、自制、寬恕與虔敬這類美德的重要性(「索米·吉傳」,93-96頁)。
1843年,吐爾斯薩希過世前,把他的靈性遺產傳給索米吉,吐爾斯薩希持續六個月進入一種三摩地狀態(靈性的狂喜),沉浸在神聖的覺知中,直到索米吉來看他之後,吐爾斯薩希才離開他人類的軀體。吐爾斯薩希最早的其中一個弟子巴巴加里達斯(Baba Garib Das),證實他師父已把衣缽傳給「孟須吉」(MunshiJi,因為索米吉波斯語學習得很好,而為當時的人們所知),索米吉接下來生命中的十五年,在一個小房間幾乎持續不斷的從事靈性練習(abhyasa)。
在吐爾斯薩希去世後,索米吉為了紀念他的前輩,繼續去拜訪哈斯拉斯。據說,有一次索米吉去哈斯拉斯時,天氣太熱,他的徒弟萊薩里格拉姆(RaiSaligram)和巴巴吉萬拉爾(Baba JiwanLal),不得不把他架在兩人中間走完最後一段行程,當時既無交通工具可利用,路面又坎坷不平。
「格蘭薩希」(Granth Sahib)收錄了拿納克古魯的教誨,索米吉對「格蘭薩希」及拿納克古魯繼承人的高度崇敬,似乎根源于其家庭傳統;誦唸錫克經典是他家庭的一種信仰,他的父親拉拉迪瓦利辛(一位薩哈吉卡特里錫克教徒,屬於拿納克潘席斯團體),虔誠的獻身於賈布吉(Jap Ji)、拉何拉斯(Raho Ras)與蘇克曼尼(Sukhmani)(錫克教經典),他以極大的宗教熱情與深深的崇敬之情每天閱讀。索米吉的祖父賽斯馬路克禪德(Seth Maluk Chand曾任都爾坡帝國的大臣)的一本波斯語版的蘇克曼尼手抄本,仍然保存在索米巴(Soamibagh)的檔案(9)裡。聖瑪特(Sant Mat)的精髓因此滲入這位索米吉身上,在後來的日子裡,至少有一次在蓬尼加里(Punni Gali)索米吉的家裡講解賈布吉時,他明確的把他靈性上的恩惠歸於旁遮普(Punjab),認為拿那克與其繼承人是靈性的泉源;帕爾圖賽希(Paltu Sahib)和吐爾斯賽希是這門內在科學繼之而來的偉大弘揚者,在下面一章裡面追溯巴巴賈瑪辛吉的生活時,我們將再討論這件事。
巴巴賈瑪辛吉的弟弟萊布林達般辛(Rai Brindaban Singh)在阿久迪亞(Ajodhia)做郵政局長,他是住在阿久迪亞的瑪汗德拉拉諾帕里的巴巴馬都達斯(Baba Madhodas)的親近弟子。他就像他的哥哥希里希夫達雅辛(Shri Shiv Dayal Singh)一樣,對「古魯般尼」(Gurbani)非常看重,並且有堅定的信念。他持續不斷的沉醉於對上主(必須漢拔Bishambar)甜美的憶念,並以優美的迭句吟唱和讚美他。這在他用烏都語寫的Bahar-i-Brindaban(10)一書中,標題為Wah-e-Guru Nama的文章構成裡面,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哦!布林達般!把一切都放到一邊去吧!
誦唸偉大的名字,Wah-e-Guru,
那不僅可以淨化你的身體、心智與靈魂,
還可以為你帶來解脫、平靜,還有喜悅。
我們還得知拉拉迪瓦利辛臨終時,他的兒子席夫達雅辛(索米吉)坐在他的榻前,開始誦唸「古魯般尼」,以便在那關鍵時刻,使他父親的注意力保持專注在那點上。
基阿尼帕塔辛(GianiPartap Singh)以巴巴波拉辛(Baba Bhola Singh)的拉達索米瑪特達潘(Radhasoami Mat Darpan)為基礎,在他世界宗教的研究中,介紹了索米吉如何逐漸成為阿格拉神聖的錫克廟麥坦(Mai Than)的常客,這座廟是為紀念第九代古魯泰巴哈都(TeghBahadur)所建立的;聖毛吉帕卡須(SantMaujParkash),原名叫迪達辛(Didar Singh),屬尼爾瑪拉(Nirmala)階級,是一位梵文大學者,他常常在那兒清晰的解釋「古魯般尼」或錫克經典。
索米吉因為與聖毛吉帕卡須的密切關係,而瞭解「古魯般尼」以及蘇拉夏白德瑜珈中「古魯般尼」的意義,後來索米吉就開始在這個聖廟開始講解「古魯般尼」。查查帕塔辛在他的生平的描述中,曾用興高采烈的措詞,生動的描繪了這樣的一場談話:
「那天,大約早晨八點,師父去麥坦的錫克寺廟。在吟誦完『格蘭薩希』裡的一、兩首歌之後,他開始闡述主題,在一種豐富與鏗鏘的聲音中,崇高的思想似乎像無盡的波濤來自一座取之不竭的內在儲水槽一樣,從他那兒湧流而出;我完全沉浸在他拂過的話語之中,剎那間,感覺被拉升到身體和身體周圍之上,無知覺於屬於世間的一切。自那天起,我馬上徹底變成了另一個人,強烈的渴望上帝,完全確信索米吉的偉大與其神聖的的使命。」(12)
過了一段時間,索米吉把聚會地點遷移到他在潘尼加里的私人寓所中,繼續用「格蘭薩希」講道(他用的這本手抄本後來被哈祖爾薩望辛吉從阿格拉帶走,至今仍珍藏在旁遮普畢斯的德拉巴巴賈瑪辛的檔案館裡);這種在他家的私人聚會演講方式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1861年印度春天節那天,由當時卡比爾和同時代的拿納克古魯所復蘇的,而由拿納克的繼承者深深紮根於「古魯般尼」的音流瑜珈的水閘門,現在由索米吉打開推向了一般大眾。
為免無神論者心中還有任何疑問,索米吉始終持續為人們印心,傳授傳統具有五種曲調的「旋律」(Panch Shabd Dhunkar Dhun)的秘密,他在離開這個世界最後一天的公開聲明,足以有效的澄清他的地位,明確而毫無疑問:
我的路是薩納姆(Sat Naam)和阿納米納姆(Anami Naam)之路。
拉德哈索米(Radhasoami)的信仰雖然是屬於薩利格拉姆(Saligram)的創造,
但是也讓它繼續,讓那種「薩桑」繁榮昌盛。
萊薩利格拉姆薩哈都巴哈都(Rai SaligramSahadurBahadur)是索米吉所信賴的其中一位誠心弟子,在後來他成為靈性領袖時,以哈祖爾馬哈拉吉著稱。索米吉去世後,哈祖爾馬哈拉吉在阿格拉市中心的皮帕曼迪(PipalMandi)繼續講道;索米吉最小的弟弟,通常被稱為查查薩希(令人尊敬的大叔),在離阿格拉三英里的拉德哈索米花園(Rdhasoami Garden)繼續工作;另外一個門徒,巴巴賈瑪辛吉,索米吉最早期也是靈性上最高的弟子,按照這位偉大的明師的指示,在旁遮普的畢斯安頓下來,振興靈性的工作,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報答拿納克古魯對這個世界的恩惠。現在我們就來詳細的研究索米吉這位最出色的靈性之子的生平和工作。